 |
背叛的征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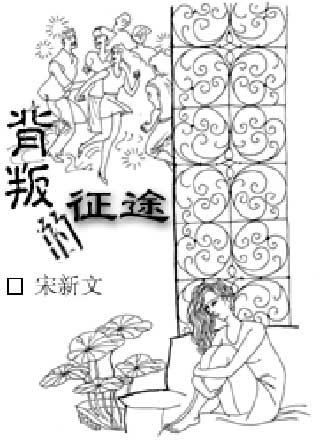
居家成专职太太那么多年,这是她第一次踏进舞厅,很有种新鲜感。在一旁的雅座坐不到一分钟,她就迫不及待地投进了舞池。她不太会跳舞,动作显得有点僵硬,身子却扭动如蛇。她疯狂地摆动,全然不管有没有人在荧荧灯光下闪动泛红或泛白的眼睛盯着她怪异地看。
这个夜晚是属于她的,属于她的这个夜晚极尽疯狂。
终于累了,她瘫坐在酒吧的沙发里,任由皮革包围。音乐仍然歇斯底里,一种酸涩的寂寞随着酒的下咽
深入到了她的肺腑。
一本有名的书中说:“疯狂的背后是难言的痛楚。”
痛楚,对于一个寂寞的居家专职太太来说,是伤口上的盐巴,无药可清洗。
丈夫已经半个月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在她辗转了一个个夜晚后,终于打扮得妖妖娆娆踏进了这间酒吧。这是一种无力的报复,但总算有些许的快感。男人为新鲜而背叛女人,女人因为男人背叛而踏上背叛的征途。
名作家说:这世界男人和女人一样,谁也不比谁更拥有背叛爱情的权利。
刚回到家,电话就催魂般响起,一声紧过一声。
“喂?”她拎起话筒抬头望墙上的钟,有些醉意朦胧。
“你去哪儿呢?”是他,她的合法丈夫。
“一个大学时的老同学生日,请我去喝了一顿。”谎话脱口而出,自然得不须再多作考虑。
“男的?女的?”电话那边的口气显得漫不经心,再漫不经心也好,微风吹过湖面还是会起皱折。
“女的,儿子三岁了。”她盯着台面上的丈夫照片,忽然有些开心。
酒精的麻醉使她说起谎来特别圆滑,感觉像是一个坏孩子捉弄他人得逞后的兴奋。
居家的女人,连谎话也成了生活的另种调味料。
“想我吗?”丈夫的情话在午夜听起来似是一朵失去水分的玫瑰。
“想。”她答得异常干脆。
她真的想过他吗?或者曾经想过也就算想了吧。
“我要过几天才回来,你自己照顾自己。”丈夫说完后匆匆搁上了电话。
每一次别离后的电话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场,没有一线爱情的影迹,也没有别离后夫妻间最应有的牵挂
话语,冰冷是仅有的特色,足以使她将女人特有的温柔在他应付式的电话里冻藏起来。
她的眼泪在午夜时刻绽放成一朵朵晶莹剔透的睡莲。顺子的《回家》一遍又一遍萦绕着她,空旷的客厅里,她蜗牛般蜷曲在落地玻璃前。
寂寞在她的脸上划下了一道道的痕迹。
寂寞没有让她变得更加美丽。
尽管她现在仍然美丽,美丽得像风中摇曳的灵芝,灵气十足而柔弱不堪。
过去的女朋友,现在的女强人樱曾极为关心地不止一次打电话给她,告诉她应以居家女人特有的警惕态
度提防她出色丈夫身边的女人。
现在的狐狸精太多了,谁也无能为力,所以年近三十的女人要特别会保护自己。樱不无疲惫地说。
樱在婚姻中始终是一个失败的角色,尽管她极想表演得出色。
任何一个女人都想有男人的庇护,女强人也不例外,但樱对婚姻越动之以情越使伤口鲜血淋漓。
结婚两次,离婚两次,女人的爱情经不起太多的折腾。
从此,樱不再谈爱情。
对男人,樱成了一块化石。
她每次都诚诚恳恳地听樱说这说那,附和得天衣无缝。可每次转过身面对丈夫宽阔的怀抱,她又热烈而
忠诚地投进去,极满足地笑笑,傻得有些像外国书籍里那些不谙世事的小天使。
樱说,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女人。
可爱,但不现实。
她的天空一向晴晴朗朗,她也一向安闲异常。以前在丈夫一去大半个月,一天一个电话的日子里,她的
依靠是那一段细细长长弯弯曲曲的电话线,她把它当成了爱情的化身,对着它喃喃细语。再后来,一次的偶
然让她发现了丈夫换洗衬衫上的一个红红的唇印。
樱的话不幸应验。
她不可能再那么一副天使般的笑容奔向丈夫。
她开始感到寂寞,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她无数次猜想他是真的如他所说忙于工作还是急着猎艳。如此的翻来覆去让她身心憔悴,但她什么也不说,埋在心里如埋一枚地雷。她依然守在家中,等待丈夫间歇性的电话,有些枯燥无味。这样的日子持续到她第二次发现丈夫的衬衣上又一个红色嘴唇时,萌发了报复的念头。
她不是樱,她无法如她那样向婚姻洒脱地挥挥手。
从小至大所受的教育告诉她,女人再怎样强大,也需要依靠男人。
女人比男人对爱情更认真,奢求更高。
更何况,她从来都未向除丈夫以外的任何一人男人多看一眼。她牢记临嫁前母亲说的一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母亲守寡了二十多年,母亲在她的印象中端庄得犹如明朝古物。
母亲的门前从来都没有是非。
那时的太阳和现在一样明媚,那时的世风仍和此时一样古朴和妖娆。
母亲关紧了她那时还算很堂皇的大门,男人们未敢强行扒开窥看。
在她幼小的时候,缘于母亲,她身受了洁白的赞誉。
懂事起,她决定效法母亲。
专一是女人的美德,虽然女人往往要为之付出许多代价。
她和母亲一样传统,她认为,这样值得。她也认为,她一定会是母亲的翻版。
她为母亲骄傲,一向都是。
于是,她耐心地等待,等待那个流荡在别的女人门口的男人的忏悔。
她准备以圣母亲般的博大去宽容那个堕入迷途的男人。
她静静等待,一声不响。
她望向丈夫的眼神清澈而悲哀,他毫不察觉。
她不会发现的,他想。
他编造的理由简单而实用,对这样一个女人,实在用不着花费太多的心机。他爱她的单纯,纵使是在拥有另一个女人的夜晚,他依然会想起她可爱的恬静笑容。
有这样一个太太,男人随时都可以轻松自如。
她在等待中终于累积了一大堆的怨气恨意,她没有理由去为丈夫的背叛找一个还算过得去的借口。
她毕竟不是母亲,她根本就不同于母亲。
母亲守着的是一种过去,她等待的是空茫的未来。
母亲为父亲从一而终是因为父亲从未背弃过他们的爱情,她守候丈夫是等着变心的翅膀重新飞回她的身边。
他有玩够的一天吗?
守着暗淡的灯光和墙上自己的影子,她总是感到彻骨的冰冷。
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她,如果男人投进了别的女人的怀抱,她还应不应该关紧自己的大门?
似今晚,她的骨子里升起了一种刺激,女人走向堕落恐怕都是以这样的心态开始吧。
堕落以后呢?
或许压根就不能算是堕落,在樱这样一个女人看来,这不过是失去爱情的女人寻找麻醉自己的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樱和母亲,两个天壤之别的女人,却都在她的心中活得一样出色。
那么,自己呢?
自己的名字叫弱者,只能是守在树下等待的角色。
第二个夜晚,衡量再三后,她还是踏进了那间昏沉沉的酒吧,打扮得更加大胆性感,也许下意识里她渴望和丈夫玩一个平手。尽管她明白,她最终等待到老的仍会是丈夫。
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在她的思维里不亚于清晨醒来时射入眼帘的第一线阳光。
她依着他而活,一如守着土地而终的老农。
她耐着性子一如既往地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她选择了另一种心态,奢望报复可以平衡自己的疼痛。
一个男人徐徐走来,这样的空间里总是有太多暧昧的情感在缓缓流动。
一个独身女人喝着烈性酒,不安分地在黑暗的掩护下东张西望,这本身就是一种极明显的暧昧。
他在她的对面坐下,连最起码的礼貌问候都没有。她忽然有些不安,在这样霸道的男人面前,她只能是柔弱的藤条。
丈夫就是在她可怜的柔弱拒绝下一拎就把她拎进了他粗糙的生活里成了他地道的妻子。
他紧紧盯着她,借着若隐若现的光线,她看到了猫一样的眼睛。她突如其来地慌张起来,想象中的诱惑明显地摆在眼前,她却唇干舌燥。
他不动声色,仅用那么一双眼睛去捕捉。
她抿了一口又一口的酒,年近三十的女人了,依然如生活在校园内的女学生一样在男人的注视下扭捏不安。
这实在有些可笑,同时她也有些愤愤不平于生活待她的不公。
他伸出了手,她一愣,丈夫的影子惊鸿一瞥掠过她的脑海。除了丈夫,她从未和其他男人有过肌肤相触。
在眼神与眼神的较量中,她傻子般由他拖向舞池。
舞池的气氛更暧昧更温情,她竭力清醒自己的同时看见了一对对亲密无间的情侣。
而他和她,本是陌路却也手牵手置身于其中。
不可思议,荒唐得不可思议。
母亲如果看到这一幕,不知会作何感想?所幸的是天堂里的母亲再也看不见了。
他带着她旋转了一圈又一圈,裙裾在变换不停的灯光下变幻着亮丽色彩。依着这个男人,她忽然有种家的厚实感,温热的气息笼罩着她,她有些痴迷起来。
灯光啪一下黑了,四围一片静默,她顿时清醒过来,对于这些可能将在黑暗中进行的活动,凡属有点年
纪的都了然于胸,她紧张得手脚发冷。
灯光再一次亮起时,她和他依然有着那么一段距离,他没有前进一步。
这让她抬起了头,有些恍惚地认为这个男人在哪里见过面,陌生里夹杂着隐隐的熟悉,这年头,不趁火打劫的男人毕竟不多了。
舞曲终于停止了,她强硬地推开那个男人,返回座位拎起提包匆匆踏出舞厅,再这样下去,谁知还会再发生什么。
樱说,现在流行一种爱情快餐,从相识到上床只不过几小时,其速度令人咋舌。
而她,一向喜欢用文火熬汤,慢慢地慢慢地,有滋有味。
也感谢母亲在天之灵纯净的眼神,终于看住了女儿洞开的心门。
推开家门,冷清扑面而来,再打开音响,还是顺子的《回家》,苦涩涨满疲惫的灵魂。
女人因为男人的背叛而踏上背叛的征途,她踏上了,却在中途落荒而逃。
她骨子里还是和母亲一样,她们流着相同的鲜血。
女人,只有洁白干净才是美丽的,母亲说。
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样,对爱情洒洒脱脱,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樱说。
两个不一样的女人,一个娴静如水,一个冷傲如冰,都活得那么好。
唯有自己无所适从不知所措。
她唯一知道的是等待也是生活,任皱纹逶迤在她的额头,将她的青春改换成另一种模样。
他呢?也终会回来,陪着她慢慢老去。
男人花心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泛爱。
她会让丈夫回来的,她不动声色地等待时机。
这是一种忍耐的智慧,对女人而言,也同样是一种冷酷的考验。
等待使女人的心在午夜成了枯萎的蔷薇,用咸咸的泪浸泡自己的爱情命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