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临时搭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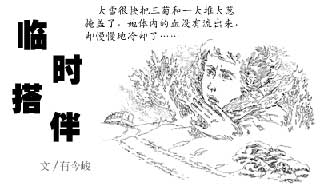
她是在蔬菜批发市场转悠时发现了他的。
当时她兜里揣了四千多块钱。在市场里边转悠,边问摊主要啥菜不?我可以去给你采购。问了几个主,都说或要西芹或要芸豆或要大葱,但要的量都不大。每个摊位一天卖不出去量很大的菜,多是几种搭配。转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找着一个大户。找大户得找搞批发的。一次能收个几吨,就值得跑一趟远途了。
数数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得抓紧时间挣点儿钱。看看天快中午,仍没个合适的目标。这时,肚子有点儿饿了,身上也有点儿冷。下边还有点儿鼓得慌,就去方便了一下。回来想先找个小摊喝碗热馄饨,就着吃个肉馅烧饼。
正盘算着,忽听有两个男人在说话。
一个沙哑嗓子说:“行,只要质量好,你给弄个十吨二十吨的,我保证全要。不但全要,而且马上付钱。”
一个粗嗓门儿的说:“我这是地道的山东章丘大葱,中国第一,也是世界第一。明清代,专门给万历皇帝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上贡的。绝对没问题,我已经运了三趟了。”
“好,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她急忙瞅那俩男人,沙哑嗓子的高大魁梧,无疑是当地的蔬菜批发大户。粗嗓门儿的矮个头,短头发,长方脸,淡眉细眼,身材愣敦实,三十四五岁模样。两个男人握了手,沙哑嗓子转身就走了。
矮个子男人刚要走,她急忙走上去,问:“大哥,你去拉葱,捎上我行不?”
“你要葱?”
“不要,呃,要!”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又有点语无伦次,“我也是倒菜的。只是山东从来没去过,咋个倒法,心里没个底儿。”
矮个子瞅瞅她,没再说啥,却转身就走。
她愣了一下,心里骂了一句,滚你娘的蛋!却又追上几步,赔着笑脸说:“哎,大哥,你就带上我不行?办成了,你从利里边提几分不就是了?山东那么远,你一个人去挺不方便的。有个人搭伴,还能互相照应一下哩!”
他又怔怔地看了看她——黑红的脸,红红的嘴唇,洁白的牙齿。蓝色羽绒服裹着健壮微胖的身材。被风吹乱的头发里还夹着一根枯黄的草叶,那大概是捆菜的稻草。
“那好,走吧!”
两个人匆匆地去喝热馄饨。她吃了一个刚从烤炉里掏出来的滋滋冒着热气热油的肉馅火烧,他吃了两个。
她问:“大哥,刚才那个要葱的,一市斤给多少钱?”
矮个子说:“一般的六毛左右,好的七毛左右。”
她眼睛一亮:“章丘那边的价呢?”
“一般的四毛左右,好的五毛左右。”
她的眼睛更亮了:“大哥,我跟你去买葱,你让那个要葱的一总收了,行不?”
矮个子犹豫了一下,说:“行。”
她冲他笑笑,抢着去付了两个人的饭钱。她知道,市场上零售的大葱已卖到了每市斤一元。如果到腊月二十五之后,价格还得上涨。自己也有几个摊贩客户,批出去一两千斤问题不大。要是春节前抓抓紧,能倒上两三趟,闹好了就能挣三四千块,发个小财了。自己干工人的工夫,干一年还挣不上五千块工资呢。两个人就在市场门外,拦了辆直达A市的长途大客车,踏上了征途。
临近春节了,车上的人挺多。两个人一时没有座。面对面站着,身子挨在了一起。她穿着棕色的高跟皮棉鞋,跟他脸对脸儿,个头儿倒好像差不多一样高了。虽隔着两层厚厚的羽绒服,她还是有点儿羞涩。他倒是挺大方也挺正派的,悄悄问她:“你叫啥名?”
“三菊?”
“骡驹子?”他嘿嘿地笑起来。
“你才是骡驹子哩!”她笑了,问,“你叫啥?”
“都叫我二能。”
“嗬,看来是挺能呀!再加四个点儿,就成狗熊了!”
他又嘿嘿地笑笑。
站了两个多小时,有几个人下车了,两个人才坐下。二能照顾她,让坐在了靠窗户的位子上,自己挨着她坐在外边。在外人看来,这俨然是一对夫妻了。
“这么冷的天,出来倒菜,也不容易呀!”
“不干咋行?人总得吃饭穿衣过日子呀!”
“有孩子了?”
“早有了,俩哩!大的是个妮儿,7岁。”
“哟,是吗?看你还像个新娘子哩!”他瞅见了她里边穿的大红毛衣。
“能大哥,你可真会奉承人!”她笑笑,小眼睛里闪出星星般的亮光来。“本来不让再生第二个了。打4年前,他爸下煤井给砸断了腿,计生委说可以照顾,才又要了一个。”
“腿伤了,还能上班吗?”
“上啥?没受伤效益好的工夫,一个月能挣1000多块。可打受了伤,矿上只给了500块钱,就再也不管了。那矿垮了,封了井。光看腿,就花了1万多块。伤好后,他也不能干重活了。俺俩就换了换位置。他管家。我跑外。”又想男人受了伤,夜里小两口热乎热乎的工夫,他的一只膝盖跪不下去。两人只好互换了位置。他虽使不上劲儿,可总算还行。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尽兴了。刚结婚的时候,她刚满二十二,他二十七,两个人几乎每天晚上都闹腾,一闹就是半夜。想着,脸禁不住热了起来。
“你一直倒菜?”
“哪里!原先我在个区办五金厂干冲床工,可厂子早就垮了,连地皮都卖了。厂长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如今一分钱生活保障金也不发,一分钱的医药费也没有。这四口吃饭穿衣咋办?孩子上学上托儿所咋办?我一开始是摆菜摊。可守着个摊子,太占人占工夫了,从一大早守到天黑,别的啥事也干不成。一天也就挣个十块二十块的。后来,我才试探着去倒的。”她说,“比大哥你是不行呀,一说就是十吨二十吨的。将来说不定还成火车的倒呢。那天看电视,一个男人就承包了一列火车。”又问,“大哥你也是下岗的?”
“也是。”却不多说。
车到A市,不走了。两人见天还不太晚,又换了个车往B市赶。
二能路熟,到了B市又换了个车带着三菊直奔章丘大葱的批发市场。
二能来过章丘多次,是倒葱的内行。看了十几户的葱,都没点头。后来在一堆大葱前站住了。
那些葱捆跟别的不一样,别的葱都是全叶全根。而这堆葱却是切了叶切了根的。只葱白就有60公分长。
葱主是个50多岁的黑瘦老头,笑呵呵地迎了过来:“老板真是好眼力。我这批葱本来是出口的。无根无叶不说,连一点儿土星都没有。粗细匀和。你看看,一根细的也没有。平均每棵半斤。因为外贸公司给的价钱偏低,还说半年以后才给钱,我不干,就没有给他们。你如果想要,价钱只比全根全叶的贵一毛,五毛。装车也不用你花钱。怎么样?”
二能动了心,侧过脸问三菊:“你看咋样?”
三菊说:“我又不懂。你看着行,咱就要。”瞅他的眼神里已有了几分柔媚。
二能转脸又跟葱主压价,压了一番压不下去。看来葱主对这个价卖这些葱胸有成竹。二能就不压了,说:“好吧!要!”
葱主咧嘴笑笑,问:“要多少?”
“十来吨吧!”
葱主大喜,立即就去找车。
三四分钟后来了一个车主,一谈,说运到冀北,运费得1600元。三菊搞不清这价是高是低,二能却说太贵。车主狠狠心,又压下去100元,二能还是说太贵。车主说不能再压,再压就干不着了,转身走了。
葱主舍不得放走这个大客户,又去找了几个车主,最低的也是1400元。二能只是不答应。
冬日天黑得快,两人跟车主这么三讨价四还价,天色就暗了下来。三菊看看表才五点半。二能瞅瞅三菊,一双细眼睛转了几转,说:“天不早了。就是找下了车,司机一般也不愿开夜车走。咱是不是找个地方先吃点儿东西,暖和暖和,住一晚好好休息休息。明天一早找车装车,傍晚就赶到家了。”
三菊就说:“听你的吧!”
两个就去找地方住宿。问了小镇上的三个个体小旅馆,却都说客满了。又问了一家“葱香”小旅店,老板娘说还有一个双人房间,一共三十块。又说你小两口住不是正合适吗。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她的脸就红了。他把她拉出门外,悄声说:“要不咱就住一个房间?你看我这人老实得像枣木疙瘩似的,还能欺负你?再说,咱俩身上都还带着‘那个’。”他伸出手,大拇指和食指捻了捻,做了个数钱的动作。
见她挺犹豫,他又说:“在火车上坐卧铺不是几十个男女老少住一块儿?大前天我从西安坐车回来,跟个大小姐还脸对脸睡了一宿呢。”
她想了想,也是。要是跟别的女人住一屋,让人给水里下了药,迷倒了,把钱偷走了,或者给勒死了,把钱抢走了……就红着脸点了点头。
女老板只登记了他的身份证,也不像大宾馆还得要结婚证,就给了把钥匙,让去住。押金是他抢着交的。她要给他十五,他说:“明天再说吧。”
住下后,他说去吃饭。两人就去门外小摊上喝龙山小米粥,吃茶叶蛋和葱花油饼。他结的帐,一共花了六块钱,她给他三块,他坚决不要。剩下的半块油饼,她舍不得扔,用个方便袋装上。
吃过饭,他说咱去溜达溜达吧。她就跟着他,踏着朦胧的夜色和昏黄的灯光,在小镇上来回走了两趟。她突然感到了一阵子温馨。八年前,她和男人还拉对象的工夫,到矿上去看他。他也是在一个傍晚领着她吃了饭在矿井、矸石山一带溜达了一圈。可回到招待所,就迫不急待地抱住了她。在那之前,她连手都没让他拉过。在那个小房间里,他和她在几分钟里就完成了按常规要经历半年或一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也就在她住矿招待所的那七天里,她怀上了女儿。三个月之后,他通过关系办出了结婚证。
刷了牙又洗了脸和脚之后,她斜倚在被子上和也斜倚在被子上抽烟的他说话。说了十几分钟,长途奔波的疲劳和室内土暖气热烘烘的温度使得她眼前迷朦起来。她打了个呵欠,只脱了毛衣、牛仔裤,穿着毛裤,扯开被子盖在身上,脸朝墙背朝外就睡了。
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梦见拉了满满的一车大葱进了冀北城。一倒手,卖给了那个沙哑嗓子的大个子批发商。批发商从腰带上挂着的长方形黑皮包中取出一大叠子“四伟人”给了她。数了好几遍也没数准,估计不是五千七就是五千九。算算挣了一千九。只跑两天,就挣一千九,行耶!她兴冲冲地回了家,给女儿、儿子换上买回来的新衣,把欢天喜地的孩子打发出去玩,又拿出了套新衣让男人换上。男人脱了脏兮兮的旧衣服,感激地一下子抱住了她。她惊异地问,哎,我走了两天你的腿咋全好了?不觉进入了佳境,又觉得丈夫咋这么沉了?才走了两天,这个瘦猴子就长了二三十斤?醒了,才觉得不对劲儿。可屋里一片漆黑,看不清对方是谁。从喘息声中听出来了,那个正忙活的男人却是自己的搭伴儿。
“你!你这个!你这个流氓!”她一挺身把他推了下去。他却从地下爬起来,又扑上去抱住了她,并伸手捂住了她的嘴。“你这小娘儿们!咋就不知道享受!你平日咋能享受上这幸福生活!你那个瘸驴男人有这本事吗?”他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堆话。她推他的手软了。可过了一阵子,破铁床老是咯咯吱吱响。他就把两个床上的被褥全铺到地上,又把她抱上去。
他说:“看着你脸儿黑乎乎的,可身上倒像葱白儿。”
她已经四年多没这么惬意了,说:“脸是太阳晒的风吹的,身上又晒不着。”
他吃吃地笑着说:“本来是倒葱的,没想到倒(捣)上蒜了。”
她骂了一声:“你这个王八蛋!”一口咬住了他的肩膀。他“哎哟”了一声,却仍任她咬着,又笑道:“你那个瘸驴男人,这工夫趴在窝里,才是王八哩!”
“那你就是个王八的蛋!”
第二天一早五点多,他还在死猪一般地酣睡。她怎么推,他也不醒。“快点儿起来,早去找车,争取今天返回去!”他仍不醒。她把手伸进被子里,揪住了他的一个地方。他才“啊”地叫了一声,睁开眼看看她,笑笑:“真是他妈的太棒了!”
她恨恨地斜了他一眼:“回去我就告诉你老婆!”
他边穿秋衣边说:“那娘儿们才不管哩!只要我一个月上交3000块钱,我就是去弄狗弄猪弄外国女郎,她也不问。”
她一听,顿时变了脸,把手一伸:“你弄了我一宿,给几千?”又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别烧包!我表弟是干法院的,我告你小子个强奸罪,非判你十年八年的!”
他顿时软了,忙赔着笑脸:“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说你!你是我的小心肝儿,行了吧?”
她冷冷地“哼”了一声:“你这狗日的,早晚得吃一粒花生米!要不就得让黑道上的给宰了!”
他去结帐。她没再提给他十五块房钱加三块饭钱的事。
早饭钱也是他出的。她也没再给他三块钱。
两个人忙去找车。问了十几辆当地趴窝的车,司机都说拉十吨葱去冀北得1600块钱以上。早上要车更贵。他不干,又领着她继续找。最后找了个司机说运费1400元,但又提出过桥费过路费得由货主出,还得管路上吃饭,他一听又不干了。
一直找到中午,也没谈成个称心的车。三菊劝他:“一千四就一千四吧,要是不耽误这半天,该赶到A市了。时间就是钞票哩!”
二能斜了她一眼:“就你大方,挣几个钱容易吗?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两个人吃了点儿饭,又去找。岂知下午的车更不好找了。
正在这时,那个瘦老头葱主急急忙忙地赶来了。隔着老远就大声吆喝:“老板!老板!”二能迎上去。葱主说:“乱跑个啥!我找到车了!车就是你们河北的!他到章丘来送货,想回去捎点儿货,不空车。”
“这太好了!”
他和她忙跟葱主老头去了大葱市场,果然见路边停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车厢上蒙着篷布。车旁站了个40多岁的司机和一个年轻的助手。
“嘿!这简直是专门给咱准备的哩!”二能兴奋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先是葱主跟二能窃窃私语,问运费1000元行不行?过桥费饭费由司机出。
二能忙说,行。葱主说那运费你先给司机还是运到家再给,你们商量。二能问了声三菊1000,怎么样?三菊说行。
二能说:“要是装10吨,咱俩一人5吨,运费每人500,行吧?”脸上绝对没有了昨晚的激情。三菊的心有点儿凉,说行。又说:“我带的钱不多,正好要4吨,你要6吨吧。”又补充了一句,“车费我拿400。”
葱主就招呼司机、二能去市场管理所的大地磅上称车,回来就装葱。二能担心葱捆中混上些半截的细的葱或夹上土块,还抽出几捆打开来看了看。这才放心地让葱过磅。
先过二能的,装了6吨。趁三菊去小解,二能又让过了2吨装上。中间隔了一层塑料布,好区别两个人的货。对司机说:“我再多给你200运费。”这时三菊来了,就让给她过,过了三吨半,车里已满满的。三菊指挥人还要往上装,司机说这车标准载重才8吨,坚决不让装了。三菊挺不高兴,坚持装了4吨。问二能:“你装了多少呀?”二能说:“6吨呀?”三菊翻了他一个白眼:“6吨咋这么多?”二能打马虎眼:“你不信,车到冀北卸下来称称,就明白了。”又说,“你要嫌少,我匀给你一吨。”
于是开车先去B市。车是大大的超了载。走在平坦的大道上,还跑不起来。碰上了坑洼,就左摇右晃。车子被压得咯咯吱吱响。司机忍不住开了口:“兄弟,装得太多了,这车吃不住劲儿。”
“没事。开吧!”
三菊已躺在了后排座位上,头枕着二能的腿,以大功告成的眼神往上瞅着。二能用手去抚摸她的脸,又把手伸到她毛衣下去捏那俩挺高的东西。司机从镜子中瞅见了,却装做没看到。
车子进了B市的北外环路。60公里的路开了两个多小时,天已暗了下来。司机说:“照这个速度,20个小时也到不了冀北。”
二能没吭声,心想开你的就是了。
北外环路更加难走,一个坑洼连着一个坑洼。车子摇晃得更加厉害。遇到个大坑,车子一歪,就像要倒了似的,司机禁不住骂了起来:“这路我走过好多趟了,绝对的是一条‘腐败路’。这修路的头儿抓起十个八个来,‘先枪崩,后审判,绝对没有冤假案’。”
二能却不理会司机的骂,低下头去,附在她耳边低声说:“到了冀北,我给那个批发商再抬抬价,每斤抬他5分钱!”
三菊笑笑,扭脸就咂了他一口。
二能又问:“狗熊的味道怎么样?比瘸驴来劲儿吧?”
三菊娇嗔地一笑,伸手揪住了他的耳朵。
过了一个收费站,司机把车停下了。下车去查看车下边,见车轮压得几乎贴住了后桥,就对也下了车的二能说:“老弟,这车不能开了!”
二能当然不干。两人争执了一番。司机说:“再往前开,我这车就得报销了。再说车也跑不起来呀!咱哪辈子能到冀北?”
三菊对这事倒不关心。她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对二能说:“快走吧,我都饿了!”又冲司机说,“你口罗嗦个啥!又不是不给你钱。开你的车就是!”
司机说:“抛了锚我可不管!”心想,我顶多爆个胎。可你这十二吨葱要是窝在路上冰成了冰棍,哼!咱看谁吃的亏大!
又开了一段路,到西外环路上。很明显是到了郊区,路上已不见了行人。只偶尔有几辆亮着大灯的轿车卡车驶过。车前的灯光里,有了无数闪闪发亮的雪花在飞扬飘动。司机瞅瞅路边有个旅店,说:“今晚别走了!天这么冷,吃点儿饭,住一夜,明儿一早走吧。这天寒地冻,深更半夜的,车真要坏到半路上,可就麻烦了!”
二能也觉得肚子咕咕叫,就说:“好吧!”
司机又不情愿地“哼”了一声:“你要是少装几吨,这工夫咱得出去200公里了。十个钟头开到冀北,住宿费不就省下了?”
三菊不耐烦了:“你老是口罗嗦个啥!出门在外,你拉葱是为了挣钱,俺倒葱也是为了挣钱。目标是一致的。对不对?要不是碰上俺俩,你这车跑空回去,不是少赚一千?行了!住一夜,明天回家,晚上让你老婆好好犒劳犒劳你!”
司机就和二能去旅店里登记。快进旅店门时,二能对司机说:“哎,哥儿们,咱事先说好的。我只付运费,别的可一概不听。”
司机听了这话,步子顿了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早知你这么抠门儿,我就是空着车回去,也不给你拉。还不够生气的哩!”
二能却不吃他这一套,也瞪起了眼:“哎,你要是不愿拉,现在你就可以卸货。我就不信,拿着钱还雇不着车!”
实际上,司机是不舍得放过这个机会的。空车跑回去,光油钱也得二百。况且,给他卸葱,起码得卸两三个钟头。白干不说,还累得贼死。想到这,又恶狠狠地斜了二能一眼:“好好!算我倒霉行不行?”
可是,当两人到服务台一问,值班小姐却说客满了,没有床位了。
两人出了店门,各打各的算盘。二能其实是不愿卸葱的,卸了葱,天这么晚了上哪儿找车去?葱本来就是一包嫩水儿,冻上一夜非成了冰棍不可。再一化冻,就成烂泥了。他瞅瞅卡车,小眼滴溜溜地转了几转,叫住了正往车那边走的司机,说:“我去跟她商量商量,卸下她的葱来。咱们走。”
“她的?”中年司机惊异地张了张嘴,“你俩不是一对儿呀?”
“啥他娘的一对儿,我昨天上午才认识她。连她叫啥家是哪里的还不知道哩!”
“那好吧!不过,这么干挺不仗义哩!”
“你甭管了!”
二能打开车门,把想法跟三菊说了。三菊一听就叫了起来:“卸我的葱?这荒郊野外的,天又黑了,我上哪儿找车去?”
二能没了辙,又说:“要不,卸下我的来,我走,运费你一个人支。”
三菊一想,自己的葱才4吨,却要支10吨的运费,不合算。也不答应。
双方僵持了几十分钟。
司机不耐烦了,下车到路边撒了泡尿,边系着扣子,边走过来说:“你俩快决定。反正不卸货车是不能跑了。”
二能点上一支烟,使劲抽了一口,把司机和青年助手叫到一边,低声嘀咕了几句。三个人爬上车,一声不吭,七手八脚地把装在车后的葱捆就往车下扔。
三菊坐在车里,开始还不知道三个人在后边干什么。后来听到地面上扑扑通通地响,才觉得不对劲儿。忙开门下车,跑到车后一看,三个人正往下扔葱捆,地上已经摞了一大堆。顿时“嗷”地叫了一声:“你们敢卸我的葱!”抓起地上的葱就往车上扔。扔了几捆,觉得不得劲儿,就叭叭扯开羽绒服的扣子,脱下来扔到一边,抓起地上的葱再往车上扔。一个女人往上扔,哪有三个男人往车下扔得快?不一会儿,塑料布后边的葱就全扔了下来。三菊扔上去的葱也全被扔了下来。二能叫了声:“走!”三个人就扑通扑通跳下了车。三菊更急了眼,像只母老虎扑上去揪住了二能,大声骂道:“你这个王八蛋!你×了姑奶奶,还要坑姑奶奶你不让我走,你也走不了!”二能甩了她几下,竟没甩开。就说:“弟妹咱好商量好商量!我给你200块钱,你再去找个车不行?”
三菊仍死死地揪住二能不放:“天这么黑了,我上哪儿找车去!我上哪儿找车去!你这个黑心肝的!我非让俺表弟把你送劳改队去!关上你十年!”
一听“劳改队”,二能不禁打了个冷战。他冲还愣愣地站在一旁的司机和青年助手吼了声:“妈拉个×的,还不快上车!”就不掰三菊揪他衣服的手了,而是伸出双手卡住了她的脖子往前一撑,三菊“呃”地叫一声,松了手。二能脚下一绊,猛地一推,三菊后退了几步,扑通一声摔倒在那一堆卸下来的葱上。
这时,车已缓缓开动了。二能飞快地跑上去,追上车,青年助手已打开了后门。二能钻进去。“砰”地一声关上车门,说:“快点儿!快开!”
司机变了档,一踩油门,车子就加了速。
三菊急疯了,从葱堆上爬起来,大骂着我操死你娘!我操你祖宗!拼了命的追了上去。只几秒钟就追上了卡车,双脚一跃,跃上了车门踏板,伸手就抓住了车门把手。二能没想到三菊能追上车,急忙摇下玻璃,叫了声:“去你娘的!”伸手一推她的肩膀,三菊仰面朝天往后跌了下去。
二能本来并没想害死三菊。可是三菊跌下去后没能站稳,车厢上的一个钩子把她猛地刮了一下,竟将她甩到了车下。两个大胶皮后轮承受着连葱带车十几吨的重量,从她的胸部和腹部压了过去。
卡车飞快地开走了,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的雪夜里。
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落下来了,也落在了三菊的脸上、大红的毛衣上、牛仔裤上、高跟鞋上。有一只棕色的高跟棉皮鞋在她身前四五米的地方站立着。她闭着眼,没有痛苦的表情,好像睡着了一般。右手里还紧握着半截折断了的葱白。
大雪很快地把她的身体和那一大堆大葱覆盖了。她体内的血没流出来,却渐渐地冷却了。
 | |
|



